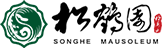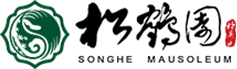冬天的时候坐在947公车上,特意选择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。
途径枣阳路,还是那片成群伫立的法国梧桐树,视线极力透过荒芜的枝干,瞥到了少年宫红色砖瓦砌成的三角顶,灰头土脸的。想起老胡曾经和我们一起待过的303室,房间不大,但一进去永远陈放着整齐的谱架。老胡退休后,或许303就被逼仄角落中的樟木箱整个装了起来。自从暑假一别后,我再也没有回去看过老胡,想到他已经不在了,心里很愧疚。
做学生的时候,每周日的晚上,我都会拎着小提琴,搭乘家门前的公车去找老胡上课。似这番的来回持续了整整8年。老胡每三年收一次学生,而我有恰巧赶上了他收学生的那一年。一切皆偶然,也确乎偶然。
起初,我们并没有直接上手去拉琴,而是按照老胡所说的,右手拿住一支铅笔,反反复复摆出持弓的姿势。黑板上,隔天见的指法排列图烙在左手四指的每一根神经上,直至今日仍能排出每种升降号对应的指形。准备工作就绪后,老胡才将一把提琴郑重地交到我们的手中,告诫我们要爱惜提琴,就如战士爱护自己的武器一般。每天近乎三小时的架琴、持弓、打节拍等在我幼时的记忆中留下了擦不去的印记。
度过了略显枯燥乏味的启蒙期,最令我头疼的便是节拍与手指之间的配合。老胡常听我拉了两段后,皱皱眉,说,“节拍打得慢了。你回去自己看着钟的秒针,它走一格,你打一拍。”而我对一切都言听计从。然而,这个弊病至今我或许仍然存在,如果老胡还在的话,他应该会再次不厌其烦地点我的名字,纠正我的过失。是啊,我多希望他还在,即便批评我一句也好。
老胡总爱在小桌前放上自己的手表,提前十分钟上课是老胡一贯的习惯。上课的时候,他会拿着板一下下地打出正确的节奏,脚也会不遗余力地打在地板上,有时我们一个班都没有他打出的拍子响。课间的时候,他总爱一个人站着演奏《渔舟唱晚》,曲调当真是“响穷彭蠡之滨”,或是解答同学们对于指法或弓法的疑惑。大部分时候他更像是家中的爷爷,和我们闲聊,用最为质朴的语言教导我们如何立身处世。
老胡的教学计划很严格,每周作业有音阶琶音、一首练习曲、双音练习,每阶段有一首协奏曲、一首中国乐曲,老胡是严格按照业余考级标准安排曲目和基本练习的。每拉一首曲子,他都会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找到这首曲子的CD,让我仔细模仿大师。练好后,还会一遍遍变着花样地和我合奏或是让我独奏。这时,他则会在这一遍遍的重复后在我的谱子上圈出注意点,错了一次的用铅笔勾画,错了两次以上的顽固错误则用红笔用力圈画,略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
最后一次见到老胡是在他的家中,彼时,他坐在藤椅上,脸颊瘦削,眼窝深凹,枯瘦得和老树一般,只有背仍像往日般挺拔。这时,他已经不拉琴了,小提琴班也都陆续解散。那天,老胡的精神不错,为那首《彼得与狼》标上了重点。临行前,他向我点头致意,“这么多年你一直是班上很认真的同学,相信自己,等你中考完,再来找我。”我想,8年来,我唯一与别人不同的就是我听话,坚持练琴。在如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学习环境中,每天挤出一个小时的练琴时间是要拼死拼活的,为此常要写作业到深夜,然后永远睡不够。
老胡,外面的人尊称胡先生。据说,他曾经是海军出身,在船上是文艺兵。他从小所受到的小提琴的教育和环境是极为苛刻的,甚至拉不好琴就意味着他以后的人生只能去做一个普通的农民,这对心高气傲的老胡来说是绝不允许发生的事。退役后,老胡就改行当起了音乐教师,教了无数学生,不乏雏凤清声之辈。
其实,我们当时的学琴水平都是很差的,老胡心里都明白。他的教学方法,如今想来,也未免僵化,他对曲谱的理解、对演奏范式的把握,也都是19世纪的。他没有教过我从乐理上去理解曲谱,只是让我去听录音,这也不是最好的办法。但是这8年,虽然相互之间的对话屈指可数,却有一种东西,我明白,他也明白。而这种东西,他已经传给了我。如果老胡还活着,我多想拉琴给他听,多想对他深深地鞠上一躬,说一声“谢谢你,胡老师!”
但老胡已经不在了。
回忆老胡
2018-09-28 09:18:02
相关资讯
阅读排行
- 1 著名沪剧演员——诸惠琴
- 2 购墓须知
- 3 购墓所需材料
- 4 感恩---生命的真谛
- 5 爱的传递
- 6 清明 缅怀革命先烈
- 7 我想握住你的手
- 8 民政局关于公墓出售寿穴的规定
- 9 回家
- 10 口哨里的感恩情